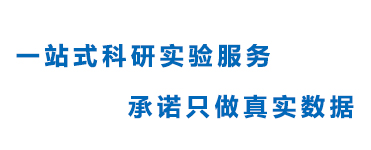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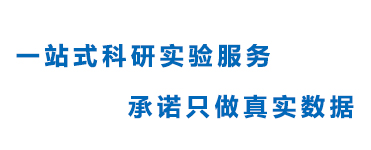
阿片类药物诱导的痛觉过敏(opioid-induced hyperalgesia,OIH)。是阿片类药物在治疗疼痛时激活体内的促伤害机制,引起痛觉敏感性增加,或使现有疼痛加重的感觉异常现象,可表现为难以控制及解释的疼痛,同时还可伴随肌阵挛、谵妄、惊厥等药物毒性反应。近年来,随着对OIH大量深入地研究,多种常见药物也被用于OIH的预防和治疗中。本文主要对OIH的分类、诊断、产生机制以及防治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多方面及深层次地理解OIH,促使临床医师在诊疗中更加合理地使用阿片类药物。
1.OIH的分类
阿片类药物均可诱导OIH,且不论给药方式和途径。单次高剂量、反复多次、长时间持续泵注、突然停药等多种方式都可以诱发OIH的出现,局部肌内注射、鞘内给药、静脉通道等不同途径也同样可以出现OIH现象。
1.1根据组织对不同刺激的感受分类
痛觉过敏可分为机械性痛觉过敏、热痛觉过敏及冷痛觉过敏。其中,相关研究H。通过对注射不同剂量和不同时间的阿片类药物所引起的OIH现象进行了综合评估,发现阿片类药物引起的机械性痛觉过敏与给药总剂量呈正相关,与暴露时长无关;而热痛觉过敏的产生与暴露时间有必然关系,热痛觉过敏多是长时间反复输注阿片类药物所致,短时间或单次给药的动物仅显示机械性痛觉过敏而未出现热痛觉过敏。目前,对阿片类药物诱导的机械痛觉过敏和热痛觉过敏的研究较多,对冷痛觉过敏的研究较少,且对于阿片类药物是否能诱发冷痛觉过敏尚无明确定论。
1.2根据敏化部位的不同分类
痛觉过敏可以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痛觉过敏。其中,原发性痛觉过敏是指由初级传人纤维的敏化引起痛觉过敏,表现为对来自损伤区域的刺激产生夸大的疼痛反应,如伤害性刺激反应阈值的下降及感受野的扩大。继发性痛觉过敏指传人的伤害性刺激提高了中枢神经系统疼痛传递神经元的反应,表现为对损伤区域外的刺激也能产生夸大的疼痛反应,如损伤区域以外的刺激也可促使脊髓背角疼痛反应增强。总之,对于痛觉区域,原发性痛觉过敏增加其敏感性,继发性痛觉过敏扩大其范围。
2.OIH的诊断
阿片类药物的使用不仅与OIH有关,而且与痛觉耐受(opioid.induced tolerance,OIT)、药物依赖性等密切相关,为临床OIH的明确诊断提出了挑战。
2.1 OIH与OIT
OIT伴随着一种潜在的OIH,二者在形成和发展中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如N.甲基一D.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NMDAR)的激活、第二信号转导系统及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的作用、中枢敏感化和神经元可塑性改变等。二者不同之处在于,OIH是指阿片类药物可使促伤害性感受通路敏化、增大痛觉敏化效应,表现为剂量效应曲线下移;OIT是指阿片类药物可使抗伤害性感受通路脱敏,使药物的效能降低甚至丧失,表现为剂量效应曲线右移,二者可有相同的临床表现(药物剂量的增加)。
2.2 OIT与药物依赖性
长期反复使用阿片类药物可引起机体对药物的生理以及心理的依赖性,停药后会出现难以忍受的周身疼痛、焦虑与惊厥发作等,渴望继续用药以追求精神满足及避免不适,即阿片类药物依赖性。Chu等提出:痛觉过敏和痛觉超敏是撤药综合征的典型表现,阿片类药物的应用可导致相应神经元敏感化和适应性改变,从而可能会出现痛觉过敏和药物依赖性。然而,药物依赖性多在长期用药患者突然停药后出现,而阿片类药物的使用过程中、加量及停药后均可诱发OIH。
综上,在临床实践中很难检测OIH:目前,临床工作者还是不得不依靠疼痛的程度变化[如定量感觉试验、VAS评分等]、阿片类药物的用量、临床症状及主观表达等来综合判断,以期减少OIH检测的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然而,OIH检测仅仅基于上述方法尚不能对OIH进行可靠的诊断,基本诊断标准的建立仍需大量的探索与研究。
3.OIH的产生机制
OIH的发生机制尚无明确定论,在OIH机制研究中出现过众多的假说和理论。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中枢谷氨酸能系统
谷氨酸是中枢神经系统中的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通过激活谷氨酸受体引起相应信号转导,控制机体疼痛的发生与发展。NMDAR是一种异源性四聚体,它主要由NR1、NR2以及NR3这三种不同的亚基构成。不同的亚基组合可形成不同的NMDAR,其中有功能性的NMDAR必需含有NRl亚基和至少一个NR2(A-D)亚基单位。NMDAR既是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性递质谷氨酸能受体,直接受神经递质谷氨酸控制,也是离子通道型受体。脊髓背角释放的谷氨酸可激活突触后膜的NMDAR,随后大量Ca2+内流,并被线粒体再摄取,产生超氧离子(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而ROS又进一步激活钙依赖蛋白激酶,不同的激酶可在不同的位点上对NMDAR进行磷酸化调节,进而控制着NMDAR通道中的电流。
这些激酶被激活后可使NMDAR的亚基NR2B的酪氨酸(tyrosine,Tyr)磷酸化,使脊髓背角神经进一步释放谷氨酸,引起脊髓突触可塑性改变和中枢敏化,最终产生痛觉过敏现象。研究发现,瑞芬太尼可诱发大鼠脊髓NMDAR的NRl和NR2B亚基从细胞内转运到细胞膜表面,导致大鼠的机械痛和热痛觉过敏;可通过激活脊髓背角神经元中的NRF-1,使NR2B亚基的表达增多,从而增加活化的NMDAR含量,导致继发性痛觉过敏的发生。
总之,阿片类药物的应用可使中枢谷氨酸能系统中的不同位点发生相应改变,从而诱发OIH。
3.2内源性神经肽
强啡肽、P物质、胆囊收缩素是与OIH关系密切的常见的内源性神经肽。阿片类药物的给予可增加脊髓强啡肽的水平,导致脊髓兴奋性神经肽降钙素基因相关肽的释放,与此同时,还会引起背根神经节P物质水平的异常增加,从而促使OIH的发生。同样,Rivat等研究发现,应用P物质皂角甙(自杀性传输)清除大鼠脊髓神经元的神经激肽-1(neurokinin-1,NK-1)受体,可减低或抑制OIH的发生。Xie等研究发现注射阿片类药物能引起延髓中的胆囊收缩(cholecystokinin,CCK)浓度增加,激活CCK受体致脊髓强啡肽表达增加,从而在脊髓水平增强伤害性刺激的传人,进而导致OIH。以上可提示内源性神经肽在OIH中的重要性。
3.3μ受体功能改变
阿片受体在中枢神经系统内至少存在4种亚型(μ、κ、δ、σ),且分布广泛而不均匀,如在与痛觉的整合及感受有关丘脑内侧、脑室及中央导水管周围灰质等区域相对密集。其中,μ受体是G蛋白耦联受体,G蛋白在OIH中起到重要作用。通常,当μ受体与抑制性G蛋白(Gi)结合时,可以产生钾离子外流,促使细胞膜超极化,从而抑制伤害性信号的传递,产生镇痛作用;当斗受体与兴奋性G蛋白(Gs)结合时,促使细胞膜除极,从而促进伤害性信号的传递,诱发OIH。Zhao和Joo研究也证明,临床相关浓度的瑞芬太尼可通过激活μ和δ受体使NMDA受体峰值电流快速、持续增强,从而产生OIH,而且随着输注时间的增加和效应浓度的增大,所产生的NMDA受体峰值电流越强,即具有球形浓度效应依赖性和时间依赖性。
总之,发生OIH时,斗受体功能发生了由抑制性向兴奋性的转变,与Gs结合,同时该作用也可促进NMDAR的开放,从而更有利于痛觉过敏的发生。
3.4脊髓下行易化
延髓头端腹内侧部是中枢下行疼痛抑制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与疼痛信息的调控。在伤害刺激尚未建立疼痛反射之前,延髓头端腹内侧部内对阿片类药物敏感的兴奋型细胞率先被激活,并投射至脊髓水平易化疼痛,同时抑制型细胞的活性下降,两类细胞活性的不平衡可能是诱发OIH的原因之一。
3.5抑制性神经递质受体系统功能改变
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是脊髓和脊髓上结构中调节疼痛的主要抑制性神经递质。输注芬太尼诱发OIH的大鼠模型中可发现神经元胞体及突起中的GABA含量下降,增加了锥体神经元对突触前刺激的易感性。同时,钠钾氯离子联合转运体(Na-K-Cl cotransporter 1,NKCCl)和钾一氯离子联合转运体2(K-C1 cotransporter 2,KCC2)是决定细胞内氯离子浓度的主要蛋白,而细胞内氯离子浓度稳态是GABA受体功能正常的基础,因此它们在OIH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3.6过氧亚硝基(peroxynitrite,PN)路径
PN由超氧阴离子与NO相互作用生成,是OIH发展中的重要信号分子。Shu等m1研究表明,瑞芬太尼可通过诱发PN的过度生成,从而激活不含铁反应元件的二价金属离子转运蛋白1引起铁超载,进而导致OIH。同时,PN可硝化灭活谷氨酸转运体1及谷氨酰胺合成酶,导致谷氨酸增多和突触传递的快速改变,从而诱发OIH。
3.7其他机制
Kumar等认为痛觉过敏具有性别差异性,这可能主要与性激素尤其是雌激素有关,雌激素可抑制脊髓内吗啡肽2(EM2,脊髓μ阿片受体的主要配体)的释放。此外,去甲肾上腺素能受体改变、遗传因素及神经免疫系统等也可能参与0IH形成。
4.OIH的治疗
随着对OIH产生机制的深入研究,很多常见药物也逐渐被用于OIH的防治中。
4.1氯胺酮
氯胺酮是一种可与NMDAR结合的苯环己哌啶的非竞争性拮抗剂,可在不同的环节抑制NMDAR的活性。相关动物实验及临床研究证据表明,氯胺酮可以促使阿片类药物引起的机械痛觉过敏和热痛觉过敏趋势降低。然而,氯胺酮应用时可伴随一定的精神症状,表现为多种不同形式的幻觉且呈剂量依赖性,因此,其抗痛觉过敏效应在I晦床应用中的可靠性及适用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质疑。
4.2右美托咪定(dexmedetomidine,Dex)
Dex是一种α2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具有高选择性及特异性。其受体选择性(α2:α1)为1 620:1,分布半衰期约5 min,清除半衰期约2 h。Dex通过兴奋蓝斑核内的仪:肾上腺素受体,降低交感活性,在脊髓水平以及脊髓上水平,通过抑制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引起神经细胞膜的超极化,抑制疼痛信号向大脑传递,并增加脊髓中间神经元释放乙酰胆碱和一氧化氮等,抑制突触前膜P物质及其他伤害性肽类的释放,通过减少阿片类药物所致的脊髓背角NR2B亚单位磷酸化上调使NMDAR的兴奋性降低,抑制钙通道使蛋白激酶C(protein kinase C,PKC)和钙.钙调素依赖性蛋白激酶Ⅱ(calcium/calmodulin-dependent protein kinase II。CaMK II)表达及磷酸化减少,从而产生抗痛觉过敏作用。因此,Dex可作为预防OIH的一种选择来改善患者的疼痛和降低阿片类药物的用量。
4.3选择性环氧合酶(cyclooxygenase,COX)-2抑制剂
COX是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PG)生物合成过程中重要的限速酶之一。COX-2主要位于核膜,呈诱导性表达。有研究显示选择性COX抑制剂可以抑制脊髓前列腺素的合成,拮抗中枢NMDAR的功能,从而减少或抑制了OIH的表达。然而,选择性COX-2抑制剂可通过抑制肾脏COX-2活性,使该通路中PGs的生成明显减少,可引起肾脏的副作用;而且还可增加心肌梗死的患者再次心肌梗死的危险。
总之,选择性COX-2抑制剂可作为抑制OIH的选择之一,但应用时应当权衡适用个体的利弊。
4.4利多卡因
利多卡因具有浓度依赖性抑制NMDAR的激活,且可能是通过抑制PKC信号转导通路实现的。Cui等研究中用雄性SD大鼠在瑞芬太尼和丙泊酚麻醉下进行足底切口手术,可在脊髓角神经元细胞中观察到conventional PKCg(cPKCg)的背膜易位增加合并机械性痛觉过敏,而利多卡因可通过抑制cPKCg的背膜易位来逆转OIH。因此,利多卡因可为临床抑制OIH提供新思路。
4.5氧化亚氮
氧化亚氮(nitrous oxide,N2O)是已知毒性最小的吸入麻醉药,亦是一种有效的NMDAR拮抗剂。N2O可以直接抑制兴奋性谷氨酸在脊髓背角的传输,也能够抑制中枢神经系统不同位点的谷氨酸反应,从而明显降低术后阿片类药物诱发的痛觉过敏。
4.6其他
布托啡诺、美沙酮、帕瑞昔布钠、纳美芬、钙通道阻滞剂及抗癫痫药等在动物实验或临床工作中也曾有报道用于抗痛觉过敏的研究中。此外,阿片类药物逐渐停药也可能会减少OIH的发生率。多种药物及不同的用药方式为抗痛觉过敏提供更多的考虑或选择。
5.结语
现在越来越多的临床工作者也意识到:阿片类药物在为我们临床麻醉和术后镇痛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选择的同时,也伴随了OIH。在人性化的医疗体系中,预防胜于治疗,及时的干预也许是减轻或抑制这种伤害性感受系统改变的有效方法。从术前药物应用、术中联合用药到术后多模式镇痛等多个方面减少OIH的发生率,与加速康复外科的理念相契合,可以最小化围手术期机体的副作用及并发症,提高康复质量,从而大大增加患者满意度。目前,OIH的产生机制和诊断尚未完全明确,其防治措施也愈显多样性和复杂性,仍需更深层次的研究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工作。
(本文转载国际麻醉学与复苏杂志2017年6月第38卷第6期)